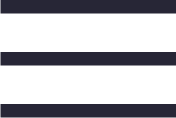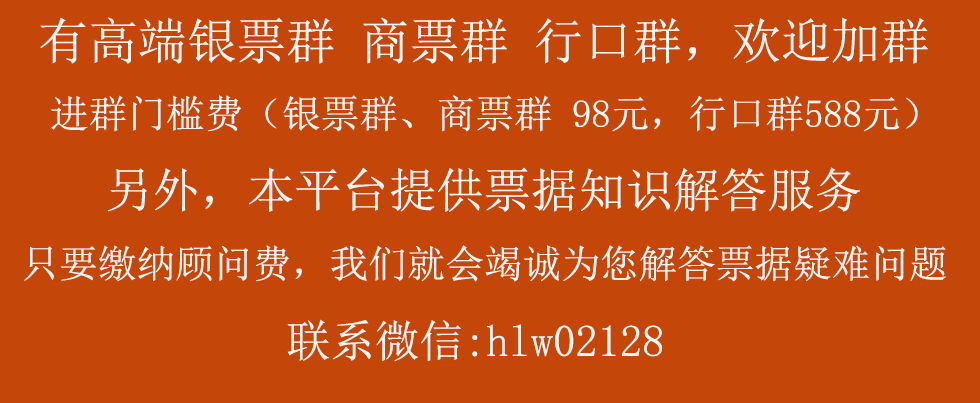
根据《贷款通则》第九条之规定,贷款依据其信用程度分为信用贷款、担保贷款与票据贴现。其中,票据贴现系指贷款人以购买借款人未到期商业票据的方式发放的贷款。另从银行会计的角度来讲,票据贴现系银行运用其资金的一项表内(资产)业务,被纳入信贷科目管理,且在银行统计存贷比、拨备覆盖率以及贷款余额时也均被统计在贷款项下,故票据贴现实为银行发放贷款的一种形式(汇票贴息即贷款利息)。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虽然票据贴现系与信用贷款、担保贷款并列的第三种贷款,且笔者在《套取担保贷款转贷牟利是否成立高利转贷罪》一文中已论述高利转贷罪中的“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包括信用贷款而不包括担保贷款,但这并不意味着票据贴现因并非信用贷款而当然不属于“金融机构信贷资金”。这是因为,法秩序统一性从来不是指同一语词在不同法域当然具有概念上的同一性,同一语词在不同法域各自的规范目的之下可能具有不同的内涵与外延。由此,刑法上“金融机构信贷资金”的界定须着眼于本罪的规范目的与保护法益,亦即票据贴现是否应当认定为“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取决于套取承兑汇票出让他人贴现的行为是否对金融机构资金安全造成危险(关于通过“法益权衡”以比例原则将高利转贷罪所保护的金融管理秩序法益限定为资金安全法益,参见《套取担保贷款转贷牟利是否成立高利转贷罪》)。
由于贴现行(包括回购式转贴现的申请行,以及买断式转贴现的转贴行)在汇票到期后得向付款行(承兑行)要求行使票据权利,故票据上的负担与风险一般系由承兑行承担(除非承兑行因故不予付款),亦即承兑使得商业信用(出票人信用)转为银行信用(承兑行信用)。若出票人未在汇票到期前足额缴存票款,则承兑行在向贴现行等付款后得根据承兑协议的约定从出票人保证金专户与其他存款账户扣款。若出票人在申请承兑时系缴纳差额(敞口)保证金(或者对符合规定的低风险担保出票人可免收保证金)且出票人其他存款账户亦不足支付票款,则差额部分由承兑行垫付(转入出票人的单位票据垫款户,计收逾期利息)。此时承兑行将向出票人进行催收,同时就出票人在申请承兑时提供的敞口担保(系办理银行承兑汇票敞口业务的条件之一)实现担保权(担保物权或者保证债权)。由此可见,因出票人未必在汇票到期前足额缴存票款,且出票人保证金专户以外的其他存款账户很可能发生变动,故在保证金与敞口担保总额不足票款的场合,汇票业务(不足票款部分,在无保证金与敞口担保的场合为全部票款)便具有信用性,该信用性票款虽不是、但相当于信用贷款,行为人对其实施套取并转贷牟利的行为便对高利转贷罪所保护的金融机构资金安全法益造成危险。由此,前述条件下的票据贴现便应当认定为“金融机构信贷资金”。
二、套取承兑汇票出让他人贴现的司法分歧与统一
司法实践对套取承兑汇票出让他人贴现的行为是否成立对“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实施的高利转贷罪原本存在分歧,但已为《刑事审判参考》第487号指导案例“姚凯高利转贷案”所统一。
关于该案行为模式的核心争议在于,行为人系套取银行承兑汇票后出让给实际用款人,再由实际用款人向贴现行贴现从而取得贴现款(即“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在这一过程中,行为人从未取得贴现款,而是套取汇票并出让牟利,银行系将贴现款直接贷给实际用款人而非经行为人转贷,这并不符合高利转贷罪中对“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先“贷”后“转”的行为流程。换言之,持票人自出票人处受让汇票后向银行贴现以实现票据权利、取得贴现款的票据行为,在形式与流程上并不等同于借款人自转贷人处直接受让银行贷款的借款行为。
从银行会计的角度来讲,票据承兑系银行的一项表外(或有资产)业务,不占用银行资金,而票据贴现才系作为银行贷款占用银行资金:亦即贴现使得汇票业务由表外转表内,此时银行才向贴现申请人(作为持票人的实际用款人)释放了银行资金。行为人所实施的套取承兑汇票并出让牟利的行为未曾占用银行资金,而真正取得银行资金的票据贴现申请则由实际用款人实施,系民事上合法的实现票据权利的行为。根据法秩序统一性原理,对于此种民法上真正具有合法性(而非实质上违法但被维持效力)的行为,刑法不应认定其具有刑事违法性(此外,汇票受让人的身份并不当然形成刑法上保证人地位,刑法自身原本便不能苛求汇票受让人承担积极审查出让人取得承兑汇票行为的作为义务)。由此,套取承兑汇票出让他人贴现的行为不成立高利转贷罪(不排除在给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时,套取承兑汇票的行为可能成立骗取票据承兑罪)。《刑事审判参考》第487号指导案例对此种观点予以收录:“在审理中有观点认为,在商业银行业务中,贷款业务和票据承兑等业务是相并列的,贷款关系与票据关系是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因此,骗取银行的承兑汇票并不等同于套取银行信贷资金。同样,持票人的贴现是实现票据权利,是与银行之间的一种借贷关系,而不是从出票人处获得贷款,因此,被告人姚凯的行为不能认定为高利转贷罪。”此种观点具有民法上形式理性的思维特征,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然而,《刑事审判参考》第487号指导案例对该观点予以否定:“不能机械地理解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而应把握高利转贷行为的本质并结合立法精神加以判定。虽然银行承兑汇票与银行贷款表现形式不同,借贷关系与票据关系在法律上也有不同之处,但银行承兑汇票是纳入信贷科目管理的,在银行内部的管理模式和性质上是相同的,银行承兑汇票贴现时使用的资金属于银行的信贷资金,票据贴现也是银行借出信贷资金的一种表现形式,因此套取银行承兑汇票然后转让他人进行贴现的实质上属于套取了银行的信贷资金。本案被告人姚凯以农垦工贸公司的名义向银行申请办理承兑汇票时,编造了虚假的交易关系、出具了虚假购销合同,采用了欺骗手段,套取银行承兑汇票后,将汇票交给用款人,然后用款人向银行贴现,由此完成了转贷并且非法获得了高利,这只是套取银行信贷资金的手段形式不同,其实质是一种利用承兑汇票贴现套取银行资金的行为,符合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的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的行为特征。所以,不能以被告人一方与银行、鞍山市轧钢厂之间具有形式上的票据关系而否认其实施了套取银行信贷资金的行为。”此种观点显然是对高利转贷罪的构成要件进行了实质理解:要么是坚持本罪中“金融机构信贷资金”乃实际用款人向贴现行申请的贴现款,而对先“贷”后“转”的行为流程予以灵活把握;要么是坚持先“贷”后“转”的行为流程,转而认为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的行为乃行为人向承兑行申请承兑汇票(基于票据的设权性、流通性等,认为套取并转让汇票及其所表彰之票据权利的行为,在实际法效果上几乎等价于套取并转让票面金额的银行贷款,即以票据承兑形式套取票款或者套取票据形式而非货币形式的票款)。
由此,《刑事审判参考》第487号指导案例已对套取承兑汇票出让他人贴现行为的定性作出了统一,即成立高利转贷罪。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姚凯高利转贷案【(2006)鞍千刑初字第101号】中被告人的涉案行为发生于1997年至1999年间,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于2006年6月29日公布并施行)增设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之前,但最高院刑二庭主编的《刑事审判参考》总第62集(于2008年10月出版)收录、评述该案并将其作为指导案例则系在此之后,故不能简单认为该案裁判系因行为时刑法无骗取票据承兑罪而不得不对高利转贷罪作实质解释,相反,该指导案例在刑法增设骗取票据承兑罪之后仍具有指导意义。
三、要件事实同一作为法域间比例原则之适用前提的逻辑
指导案例对司法实践的作用不言而喻,虽然前述不成立高利转贷罪的观点具有一定合理性,但与其“固执”地不认可指导案例的裁判结论,不如认真思考和发掘其裁判逻辑。
具言之,前述不成立高利转贷罪的观点具有民法上形式理性的思维特征:民法看关系。其将套取承兑汇票出让他人贴现的整体行为流程区分为出票人与受票人之间的票据转让关系以及受票人与贴现行之间的票据贴现关系,认为在真正取得银行资金的票据贴现关系中,实际用款人实施的贴现申请系民事上合法的实现票据权利的行为;同时着眼于行为人参与的票据转让关系,因其不涉及对银行资金的占用而不认为其成立高利转贷罪。
而《刑事审判参考》第487号指导案例则具有明显的实质理性的思维特征:刑法看行为(虽然在刑法学内部,实质刑法观与形式刑法观在一定程度上向来具有紧张关系;但与民法相比,刑法通常还是具有相对实质化的倾向)。指导案例对行为人套取承兑汇票出让他人贴现的行为作实质理解,认为从整体行为流程观察,该行为模式本质上相当于从承兑行套取票面金额的贷款(因贴现行得要求承兑行付款)转贷于实际用款人,从而该当于高利转贷罪的构成要件。
那么,该指导案例的裁判逻辑是否违反了法秩序统一性原理关于刑法不干预民事合法行为(指真正具有合法性、而非实质上违法但被维持效力的行为)的要求?不难发现,前述被民法评价为合法的仅是实际用款人向贴现行申请贴现以实现票据权利、取得贴现款的行为,换言之,对于套取承兑汇票出让他人贴现的整体行为流程,民法仅是将其中的贴现环节评价为合法;而指导案例的裁判逻辑则是着眼于行为人套取承兑汇票转让他人贴现的行为全流程,将整体行为评价为刑事违法。既然就该问题,刑法与民法所评价的要件事实并不同一,那么也就不存在民事违法性(就同一要件事实)以比例原则限制刑事违法性范围的问题,亦即待评价要件事实同一系法域间以比例原则限定违法性与处罚范围的前提。
仍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为例,为保护无过错的出借人或者投资人能够依据合同主张完满权利,民法对本身具备有效要件的具体民事合同认定为有效,但这并不意味着民事上的这一效力判断否定了借款人或者融资方吸收存款行为(以一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概括故意数次逐一吸收具体投资人存款)的违法性,更不能排除行为成立刑事不法的可能性:此系着眼于对具体投资人逐一实施的吸收存款行为,认为民法上违法判断与效力判断的分离可能导致有效性与犯罪性的并存(一个形式上有效而实质上违法的行为完全可能成立犯罪)。换个角度观察,若着眼于不法的“量”的积累,认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在刑法上的可罚性根据在于“借贷的集合”而非组成该集合的具体民间借贷,则民法仅是将具体民间借贷合同认定为有效,而刑法则是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整体事实评价为犯罪:就该问题,刑法与民法所评价的要件事实不具有同一性,因此该刑法评价也就并不违反法秩序统一性。譬如,在张双兰、许奎南民间借贷纠纷案【(2019)最高法民申5053号】中,最高院认为:“就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而言,涉及行为人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存款或者非法集资。行为人向不特定对象吸收存款或者非法集资往往表现为与不特定对象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当这些民间借贷达到一定规模并扰乱金融秩序时,刑法才对行为人所涉及的民间借贷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罪与非罪的评价,但其中某一具体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并不因此当然无效。”
四、套取承兑汇票出让他人贴现的其他问题
(一)套取承兑汇票出让他人贴现的违法所得计算
如前所述,若出票人未在汇票到期前足额缴存票款,则承兑行在向贴现行等付款后得从出票人保证金专户(冻结)与其他存款账户(可能发生变动)扣款。由此,保证金具有债务人(出票人)动产质押的属性,承兑行得就保证金优先受偿,故票款中与保证金等额的部分(无授信额度部分)并不会对承兑行资金安全造成危险,不应计入高利转贷罪中的“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在全额保证金的条件下,不成立高利转贷罪)。若出票人系缴纳差额保证金(或者对符合规定的低风险担保出票人可免收保证金),则票款中无保证金覆盖的敞口部分(授信额度部分)便需要出票人提供担保,敞口中的有担保数额同样不会对承兑行资金安全造成危险,亦不应计入“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在足额敞口担保的条件下,不成立高利转贷罪);仅在保证金与敞口担保总额不足票款的场合,该不足票款部分(在无保证金与敞口担保的场合为全部票款)具有信用性,虽不是、但相当于信用贷款,行为人对其实施套取并转贷牟利的行为便可能对承兑行资金安全造成危险,因而应计入“金融机构信贷资金”。
由此,票款一般相当于担保贷款,对套取承兑汇票出让他人贴现的行为应当参照套取担保贷款转贷牟利行为的区分规则予以认定。若保证金和(或)敞口担保已覆盖票款,则参照足额担保贷款,票款全部不应计入高利转贷罪中的“金融机构信贷资金”,该条件下套取承兑汇票出让他人贴现的行为不成立高利转贷罪。若保证金与敞口担保总额不足票款,则参照非足额担保贷款,即区分票款总额中的有担保数额(差额保证金数额、非足额敞口担保数额,不计入“金融机构信贷资金”)与无担保数额(不足票款,计入“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后根据票款总额中无担保数额的占比,计算全部汇票出让所得中相同比例的数额,此即票款中无担保数额所对应的高利转贷罪的违法所得。譬如,出票人缴纳300万元保证金,并提供实际价值500万元的担保,自银行套取1000万元承兑汇票,则应当认为票款总额中有800万元出自有担保数额,仅有200万元出自无担保数额而应当被认定为“金融机构信贷资金”,由于该无担保数额200万元占票款数额1000万元的1/5,故应当将全部汇票出让所得的1/5计为高利转贷罪的违法所得。当然,若银行工作人员在无保证金与敞口担保条件下承兑(可能成立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等),则作为例外,可类比信用贷款,票款应全部计入“金融机构信贷资金”。
(二)基于现实司法分歧的辩护策略选择
需要承认的是,虽然笔者认为票款中的前述有担保数额(保证金数额、敞口担保数额)不属于高利转贷罪中的“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参照担保贷款),但刑事审判中确实存在不区分信用贷款与担保贷款(包括不区分非足额担保贷款中的无担保数额与有担保数额)而将二者一律认定为“金融机构信贷资金”的做法(也有观点认为此系当前刑事审判的通常做法):若依此法,则对票款中的无担保数额与有担保数额将不予区分而一律认定为“金融机构信贷资金”。
鉴于此,在具体案件中,应当基于该司法现实,本着对当事人充分负责的态度,灵活选择辩护策略。首先,依据前述理由,若保证金和(或)敞口担保已覆盖票款,则认为票款全部不应计入“金融机构信贷资金”,争取就高利转贷罪作无罪辩护;若保证金与敞口担保总额不足票款,则在计算违法所得时,应当扣减票款中有担保数额对应比例的汇票出让所得。然而,若前述无罪(或者扣减违法所得数额)意见确实无法被采纳,则退而求其次,通过论证对票款中的有担保数额(在保证金、敞口担保覆盖票款的场合为全部票款)实施套取并出让牟利的行为不会对承兑行资金安全造成危险,或者在将金融管理秩序法益限定为资金安全法益的意见同样不被采纳的情况下,通过论证前述行为不会对广义的金融管理秩序法益造成重大危险(未侵犯该广义法益中最具通常意义乃至重要价值者,即资金安全),从而争取从宽处罚或者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罪轻结果。
(三)套取承兑汇票出让他人贴现的犯罪形态
如前所述,《刑事审判参考》第487号指导案例对套取承兑汇票出让他人贴现的行为流程作实质化的理解,其认为“银行承兑汇票贴现时使用的资金属于银行的信贷资金,票据贴现也是银行借出信贷资金的一种表现形式,因此套取银行承兑汇票然后转让他人进行贴现的实质上属于套取了银行的信贷资金。本案被告人姚凯以农垦工贸公司的名义向银行申请办理承兑汇票时,编造了虚假的交易关系、出具了虚假购销合同,采用了欺骗手段,套取银行承兑汇票后,将汇票交给用款人,然后用款人向银行贴现,由此完成了转贷并且非法获得了高利,这只是套取银行信贷资金的手段形式不同,其实质是一种利用承兑汇票贴现套取银行资金的行为”。亦即,该指导案例的实质化逻辑要么是坚持本罪中“金融机构信贷资金”乃实际用款人向贴现行申请的贴现款,而对先“贷”后“转”的行为流程予以灵活把握;要么是坚持先“贷”后“转”的行为流程,转而认为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的行为乃行为人向承兑行申请承兑汇票。
此种实质化事实上掩盖了一个重要问题:行为人亲自实施的套取行为系以承兑汇票为对象,而取得“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即贴现款的行为则为实际用款人所实施的贴现申请行为,那么,对高利转贷罪的实行行为起点(着手)即“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究竟如何认定?不难发现,行为人的着手时点被前述实质化所模糊和回避了。
具言之,就法定的犯罪构成而言,高利转贷罪系典型的复行为犯,要求一“贷”(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一“转”(高利转贷他人)共同构成其实行行为。若认为行为人套取承兑汇票的行为系着手,则要么导致汇票承兑与汇票贴现的混淆(如前所述,将申请承兑理解为以票据承兑形式套取票款或者套取票据形式而非货币形式的票款),要么导致实行行为中的一“贷”被拆分为申请承兑与申请贴现两个行为并分列于一“转”的前后(将套取票款拆分为套取承兑汇票与取得贴现款两个步骤)。
若认为行为人在实际用款人申请贴现时系着手(认为行为人套取承兑汇票的行为仅使汇票进入一级市场流通、开启了汇票流通状态,但实际用款人申请贴现、使汇票进入二级市场的行为才直接使得票款被“置换”出来的资金占用事实得到现实化,或可援用间接正犯理论理解行为人利用实际用款人作为其着手的“工具”),则导致在申请贴现行为之前发生的套取承兑汇票行为成为预备行为,这与其作为高利转贷罪的两步构成要件行为之一的法定属性相矛盾,同时也导致高利转贷罪由法定的复行为犯转为单行为犯。进一步延伸,若第一手受票人(直接从行为人处受让汇票者)并未申请贴现,而是继续向后手出让汇票,甚至该后手亦可能不申请贴现而继续向无限多后手出让汇票(汇票付款期限允许范围内),则只要尚未等到某一级后手申请贴现(或直接向承兑行提示付款),那么行为人便没有着手而仅仅是预备。然而该场合下,行为人早已完成需要其亲自实施的套取汇票并出让的行为,且早已收取汇票出让款,对其是否着手的判断竟然需寄托于未来不确定后手的贴现申请,这实在难谓妥当。
此外,该指导案例对行为流程的描述似乎系以实际用款人取得汇票贴现款之时(此前行为人已收取汇票出让款)作为行为人高利转贷罪的既遂时点,其理由在于“由此完成了转贷”,即构成要件要素此时齐备。然而,这同样值得商榷,恐难言之凿凿。具言之,以取得贴现款之时为构成要件要素齐备,系以申请贴现为实行行为之一部或全部。如前所述,若以申请贴现为实行行为之一部,即以套取承兑汇票为着手、以汇票贴现为既遂,则导致实行行为中的一“贷”被拆分为申请承兑与申请贴现两个行为并分列于一“转”的前后。若以申请贴现为实行行为之全部,即以申请贴现为着手、以贴现为既遂,则与高利转贷罪作为复行为犯的法定属性相矛盾,且导致对行为人是否着手以及既遂的判断需寄托于未来不确定后手之贴现申请的不妥当结论。但反过来讲,若以行为人套取、出让承兑汇票并取得出让款之时作为行为人高利转贷罪的既遂时点,则事实上系单独以套取承兑汇票为高利转贷罪两步构成要件行为中的一“贷”(如前所述,将申请承兑理解为以票据承兑形式套取票款或者套取票据形式而非货币形式的票款),虽然吻合了高利转贷罪的实行行为构造(以出让贴现的故意实施套取并出让承兑汇票的行为本身便内涵着承兑行可能的票款损失风险,具备行为不法),从而解决了前述以贴现为既遂所存在的问题,但仍导致汇票承兑与汇票贴现的混淆。当然,若采二元论的行为无价值论的立场,认为既遂的成立同时需要具备危险意义上的结果不法,则既遂时点又要延后至未来不确定后手的贴现之时,甚至需要进一步延后至贴现行(或者未贴现的最后一手受票人)向承兑行提示付款之时(此时将直接对承兑行资金造成最为现实紧迫的可能风险),则又会落入前述以贴现为既遂的窠臼。
以上均为对套取承兑汇票出让他人贴现之行为的实质化认定所导致的法解释学矛盾。